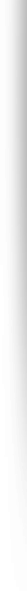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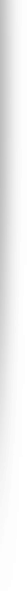
|
导语:2025年9月8-10日,索菲亚大学超个人心理学硕博士研究生在上海的立达学院举办了首次线下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超个人心理学与中国智慧传统的关系。约80-90位学生线下出席,10多位中美教授授课。博士生在9月30日之前提交1000-2000字的体验报告。我和金志芳博士从60多位学生的作业中物色了十几篇,将由汪子君编辑后发表在《内外讲习所》公众号,以期跟更多的同学和校外同行分享。这些作者有的参加了地面的研讨会,有的观看了研讨视频后提交了作业。同学们都愿意发表自己的报告。本系列中第1篇和最后1篇不属于正式的作业,因其独有的特色也纳入本系列分享给大家。
|
硕博士闭门研讨会作业之外的两个反思
蒋轶佳
1:打滚能治愈身心吗
在线下的闭门研讨会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高鸽老师的课程,非常有趣,上来就让大家就地打滚,从舞蹈教室这一头全身平躺滚到另一头,非常形象的展示了什么叫做“你给我滚”!话说从十岁之后,我就没有贴着地面长时间三百六十度全面积接触地方的“滚”。步入青少年后,我们和地面的接触更多是坐着,或者仰面躺着,随着我们不断成长,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也不断提高着我们的道德水准,“滚”这样的行为如果出现在“小草静静的生长,请勿踩踏”这样的标语下,绝对属于粗鲁和道德败坏的行为。在教室“滚”完以后,我除了全身酸爽,还伴随着轻微的大脑眩晕,只是内心在那一刻却多了一丝平静。
对于艺术疗愈,之前我一直有些困惑。我们如何理解艺术本身的疗愈性,与艺术性方法实现的疗愈,两者之间的区别。艺术本身的疗愈性,这是艺术自身特点决定的,艺术带给人类的快感和愉悦,人类看到或者感受到美好事物总是开心的。而艺术性方法实现的疗愈是把艺术作为一种媒介一种手段,类似于其他心理治疗的手段,比如叙事治疗,实现并完成了对于个体的疗愈。治疗和愈合,从英语角度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语,而中文的疗愈经常是两个字的合二为一。
艺术自身的疗愈性,比如绘画、舞蹈、音乐,它追求的是艺术的完美性、技巧性,追求一幅完美的艺术作品,超高技巧的作品,它的可观赏性、它令人愉悦的快感。并且艺术作品本身是属于艺术家的表达,欣赏者的解读也许添加了自己的理解,但是核心仍旧是艺术家思维的表达和表现。艺术作品自身的疗愈性,无论绘画、舞蹈,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永远是主角。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论艺术疗愈时,我们体会更多的是艺术本身的疗愈性。
而艺术性方法实现的疗愈才是真正的艺术疗愈,它的核心对象是来访者,艺术仅仅作为一种媒介或者通道,无论绘画、舞动、音乐,艺术都只是一种表达与沟通的形式(郭海平&郭呈如,2024)。艺术疗愈是要“心魂和自我”同时参与才能实现的道路,放弃自己艺术创作的品质,可以说,治疗性艺术是“被牺牲的艺术”,疗愈性绘画不是通过画面的艺术性达成自己的目标,而是在画面形成的过程及伴随的体验实现(玛格丽特,2020)。如果我们认为“表达即疗愈”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艺术疗愈提供了一个非语言的沟通心魂及表达自我的方式和机会,而不是向外界展示技巧性和艺术性。
下次再遇到特别不开心的事情,大家一定记得边说边做:“给我滚!”
2:无条件积极关注是一种平和心理学吗?
刘天君教授在工作坊中介绍了“移空疗法的超个人心理学因素”,由于谈到了“心理空境”,在交流过程中,我作为外行提出了一个外行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积极心理学,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果积极心理学非常好用,那么消极心理学是不是同样可以实现价值?”
按照我自己对道家“不用心”粗浅的理解,我个人会认为积极心理学有太多的前置价值判断,比如乐观、感恩、希望是比愤怒、悲伤、焦虑“更好”的。假如我们把悲伤被划到“消极情绪”,那么强行欢颜是不是可能会更加扭曲。
刘教授回应我说,有一位中国学者提出过“平和心理学”,他认为平和是更好的状态,积极心理学类似于直接到达“1”的状态,平和心理学是0和1之间的状态。(特别说明:由于是现场提问和交流,本人的记忆和记录也会存在偏差,上述内容仅代表我的理解,并不能完全代表或者代替刘天君教授本人对于相关内容的学术性阐述和理解),会后我再次向刘天君教授请教,他告诉我该学者叫何庆元。
从何庆元博士的论文和期刊文章,他并没有直接使用“平和心理学”,而是使用“平和倾向”的学术用语(特别说明:由于我看到的文章很有限,未作深入研究,并不能完全代表或者代替何庆元博士本人对于相关内容的学术性阐述和理解),他认为“平和倾向在认知维度上表现为理性思考和解决问题;在情绪维度上表现为情绪相对平静,自我调节能力强;在意志维度上表现为动机的强度适中,综合考虑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在行为维度上表现为做事稳重,不急不躁,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格倾向概念。”(何元庆&张敏, 2021, p65)
同样,何博士认为“积极情绪的拓展构建理论可以帮助解释平和情绪对合作行为的积极作用……平和状态下的个人更具有安全感和满足感,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平和可以促使个人积极感知他人,对他人的产生正向知觉” (何元庆&张敏,2021, p66)。
这与刘天君教授课上解释的情绪在[0,1]之间的动态平衡状态非常一致。非常巧合,郑日昌教授在本次报告中阐述了罗杰斯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关系三原则:真诚(congruence / genuineness)、共情(empathy)与无条件积极关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UPR)。
我个人的理解,无条件积极关注:就是将所有的积极和消极都认为是积极的,那么这个时候积极本身的含义就是已经被超越了,积极和消极根本上都消失了。在UPR中,来访者的全部经验——包括愤怒、嫉妒、羞耻、冲突、矛盾——都被允许被表达、被承认。治疗师不能因为“这是消极的情绪/行为”而贬低来访者的价值。因此,在UPR的框架下, “人就是人,体验就是体验”,无论其情感色彩如何,都值得被理解和接纳。当一切都可以被接纳,“平和”是不是也就在此刻诞生了呢?
当自己回顾这些的时候,发现自己读书太少了,如果我事先知道“平和心理学”或者“平和倾向”,如果我事先仍旧清晰的记得罗杰斯三原则“无条件积极关注”,那么我向刘天君教授请教的问题也许应该是这样:您觉得无条件积极关注是不是平和心理学一种核心表达方式?或者,无条件积极关注和平和倾向对于积极与消极的理解会有什么共通之处?(简单用关键字搜索了何博士的论文,里面并没有提到人本主义,略感意外,也许我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方向。)
参考文献:
郭海平&郭呈如.(2024).从原生艺术到原生艺术治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何元庆&张敏.(2021).中庸思维在大学生平和倾向与合作倾向间的作用,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玛格丽特·赫思嘉.(2020).艺术治疗基础(成娟译本), 三元翻译社.
带着遗憾继续向前
-超个人心理学与中国智慧传统研讨会感想
毕言琳
因为带新生军训,我错过了线下研讨会。这些天,我的时间被口哨、被汗水、被手机微信里无数个工作群、也被五十几个十四五岁孩子的一句句“老师”撕裂成碎片,又层层叠叠杂乱无章地填满每一个阳光与黑暗交替的日日夜夜。深夜回到宿舍,我才能打开电脑,关闭所有工作相关的窗口,认真观看研讨会视频,生怕学生突然来敲门。彩方老师的声音温柔而有磁性,仿佛是一首久违的老歌,瞬间抚平了我这些天的狂躁与不安。当彩方老师说“狂喜之后还得洗衣服”时,我听到了台下的笑声,我也跟着笑了。我忽然就踏实了,所谓超个人并非飞向云端,而是落回地面时仍能携带天空的气味,所谓成长,也不是等所有伤口结痂才启程,而是带着不完美、带着遗憾、带着没愈合的疼,继续把衣服洗净、把课程排好、把学生的名字一一记住。
彩方老师用自身叙事把身体的‘弱点’公开在学术场域,提醒我在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同样需要首先承认成长失败的合法性。分数落差、情绪风暴、亲子关系撕裂、校园冷暴力等等这些创伤往往被量化表格概括为异常值,可只有研究者先允许自己有缺口,才会在访谈里真正接住青少年的不完美。我已在这个学校任教八年,当过七个班级的班主任,每年都会把班级量化写进年度目标,也会把心理测评显示“警戒”的学生姓名登记在我的工作日志中。如今想来,那些量化数据,那些警戒危机是我自己的盲区,我恐惧失控,于是用数据规训学生,也在规训自己。原来我也是制造青少年焦虑的同谋。只有研究者自己先展示出裂缝,才能照见他人的光。质性研究不仅是教育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也是实践中与青少年合作的工具。坐下来听少年把话说完,允许眼泪、允许沉默、允许“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与他们共写生命脚本,在生成的故事里,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一起被重新叙述。那一刻,分数可能依旧、校规仍在,但空气已经不一样,它多了被倾听的温度,也多了继续向前的余地。
彩方老师说辟谷体验后,体重又长了回来,我看看自己渐渐松垮的裤腰带(军训九天,我跟着掉了五斤),一开始是感到高兴的,随后又担心长回来。转念再一想,又突然释怀,一切都是恰如其分的存在。如果班主任必须是铁面无私的机器,那学生只是每天在冰冷地伪装。真正的教育,是一切都是忽然释怀:若班主任必须是铁面无私的“完美机器”,学生学到的只是伪装。真正的教育,是我陪他们一起带着赘肉、带着想家、带着没叠成豆腐块的被子,继续把六点哨子吹到最响。
超个人心理学最大的价值,恰恰不是它更高,而是它敢于更低,敢于承认不完美,敢于把裂缝留在原地,甚至把裂缝当作入口。接受了多年的“左派”实证科学洗礼,我曾认为只有可重复性是科学验证的唯一标准。然而超个人心理学拓宽了我对科学认知的边界,“重复不了”不是学术投降,而是对复杂性的敬畏。它必须保持开放,必须不断自我质疑,必须随时准备修正甚至推翻自己。也正因为此,它反而比某些已经固化的学派更有生命力,它允许质性叙事与量化数据同桌,允许禅修与脑电同室,允许神秘与实证并肩。不完美,让它保持流动;裂缝,让它持续呼吸。
超个人到底是什么?我依旧会在半夜的操场,对着月亮问自己。儒家言“日月至焉而已矣”,道家言“大成若缺”,禅宗更直截“不求圆满,当下即是”。缺陷、反复、烦恼皆修行场,它与我同在,它在我仍鼓胀的小腹,在学生没叠成豆腐块的被子,在不那么整齐的队列。我们都不完整,我们终将带着各自的裂缝继续前行。可正是这些裂缝,让天空得以照进来,也让我得以彼此看见。
 中文版
中文版 English
English

